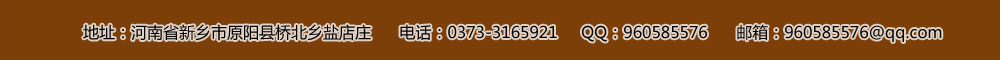神农尝百草,蚩尤尝百兽谈谈中国人吃野
——长安诗社
专栏——
神农尝百草,蚩尤尝百兽谈谈中国人吃野味的文化基因壹在一般印象中,吃野生动物只是极少数人所为,也绝非中国人的专利。然而,不到二十年间,吃野生动物在神州大地上已经两度构祸。一切现实问题都是历史问题,我们不妨在历史中寻找根源,探讨一下中国人吃野味的文化基因。有本书大家一定都听过书名,却没几个人翻开看过。我说的就是《山海经》——号称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集。其实,与其说是神话集,不如说它是一本充满了奇异幻想元素的地理志。书中除了共工、刑天、夸父、后羿这些上古大神外,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兽。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为避免麻烦,我就不讨论这些怪物的真假了,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过,古人看待这些怪物的角度,却非常值得注意。试摘抄原书第一章内容: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复生,食之无肿疾。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
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尚鸟)(付鸟),食之无卧。古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兒,能食人,食者不蛊。
其中多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鸯鸳,食之不疥。
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谁都逃不过一个“食”字。就连苦苦修行到“能食人”的九尾狐,也被人发现“食者不蛊”(吃它的肉能抗蛊毒)——食物链的顶端,岂容别的物种酣睡!九尾狐英国作家J.K.罗琳的著名奇幻小说《哈利波特》中,巫师界有一本非常普及的魔法教科书《神奇动物在哪里》,地位相当于中国巫师界的《山海经》。不过《山海经》对神奇动物的记载可不会止步在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和“在哪里”,我们更着眼于“神奇动物能吃吗?”“神奇动物好吃吗?”“神奇动物怎么吃?”吃这些神奇动物可不是为了果腹或者解馋,而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有着普通食物所不能提供的神奇功效,吃掉它们就可以“善走”“无肿疾”“不妒”“不疥”“已(停止)痔”……这不是巫师界的教科书是什么?而且翻遍《山海经》,所有动物吃掉后的功效都是积极的,能防毒治病,能获得超能力,没有一样东西是吃了之后生疮长疥得肺炎的,看来老祖宗对自然界真是非常信任。虽然我说不讨论这些神奇动物的真假,但是面对如此详尽的食用功效,还是忍不住要问作者一句:这样那样的功效,你是怎么知道的?中国古代的医生,告诉人们世上的植物都有神奇的药效。怎么知道的呢?是神农氏尝遍百草,一样一样试出来的。不论真假,起码逻辑上算是说得过去了。然而,这个传说却没有提到神奇动物们的药效是从何得知的。大抵那些怪物反正他们也搞不到,所以就无须解释了。于是我干脆大胆杜撰了这个题目——神农尝百草,蚩尤尝百兽。用贾宝玉的话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就假设是蚩尤尝遍了百兽,为我们总结出一样样神奇的功效吧。神农尝百草,蚩尤尝百兽,分别测试出了百草、百兽每一样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神农也好蚩尤也罢,他们是如何事先得知百草、百兽就一定蕴含着对人体的神奇作用呢?说来话长,这才是最有趣的问题。远古先民们钻木取火,结绳记事,好不容易填饱了肚子后,就开始认真思考这个世界以及人类自身了。大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也就慢慢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西方人思考的是“逻各斯”,是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客观规律,人类自身——人类的肉体、灵魂和认知——也是“万事万物”之一,是思考研究的对象。中国人思考的是“道”,是万事万物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万事万物如何相处直至融为一体,“天人合一”。人自身是思考研究的主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也。”万事万物只有与人发生关系,才会被纳入思考研究中去。明代有个了不起的王阳明先生,至今还有无数粉丝。他年轻时学习朱熹的理论,要“格物致知”,于是去院子里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格到生病也没有“致知”,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人,竹子是竹子,竹子跟人没有发生关系,这里就不存在“道”,当然也就无从致知。后来王阳明学问大成,再谈“格物”就是另一番境界。他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句话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花与人通过“看”这个动作发生了关系,“道”于是就生成在其中了。哲学太抽象了,不过放心,本人没什么学问,讲不出高深难懂的东西。“万事万物与人的关系”,往浅了说,就是万事万物对人有啥用。前面说了,西方人问“神奇动物在哪里?”中国人则问“神奇动物能吃吗?”“神奇动物好吃吗?”“神奇动物怎么吃?”“能、好、怎”总结起来就是一句“有啥用”。再说回《山海经》,其实书中也有不少人类不吃的东西,还是摘抄第一章: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
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
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为畏。
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如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
这里的动植物侥幸没有被纳入食谱,但是他们却别有一番悲惨命运,要被人类“佩之”。“佩之”不知具体是怎么一个操作,就当是将它们的羽毛皮角佩戴在身上吧。虽然同样是个死,但是做成物件也算另一种永生,总好过被当作食物或者药材吃掉。相比之下,这些才是真的幸运: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
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斫木,见则县有大繇。
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
这些神奇动物不用被“食之”或者“佩之”,它们只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人们面前,老百姓一看,“哦,要发大水了”,“哦,要有旱灾了”……他们与人类发生关系的方式是“见”,就跟王阳明的花一样。至于这一见之后会不会惨遭扑杀,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不论是“食之”“佩之”还是“见”,所有动植物被记录在《山海经》中,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要跟人类发生什么关系。我们的老祖宗不会平白无故去思考研究动植物,一定要问“对人有啥用”。人类与自然万物发生关系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简单加工来制作生活用品,可以通过接触或模仿来获得神秘力量,可以通过审美来获得精神愉悦……尽管这些方式越来越高级,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动作,还是吃。所以当神农、蚩尤面对自然中的百草、百兽,要去发生关系,要去格物时,他们不约而同采取了“尝”的方式。神农尝百草,蚩尤尝百兽,这实则昭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起点。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即便没学过什么古代文化知识,也能从历代延续下来的话语中,从饮食习惯和健康理念中,不知不觉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越蠢的人,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提取的东西越原始,越低级。吃野味,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最低级的映射。贰有人说,当代中国最大的议题,就是“中还是西”“传统还是现代”的选择问题。西方人认识自然、解构自然,创造出自然里没有的事物。中国人拥抱自然,融入自然,向自然中取用。我们确实无法逃避这个价值判断:是中国的东西好呢,还是西方的东西好呢?前一阵子网上有个讨论:牛顿跟孔子哪个更伟大?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网友把票投给牛顿。其实网友们既不认识牛顿,又不认识孔子,也没弄清楚“伟大”。牛顿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中都只是个符号而已,一个代表“科学技术”,一个代表“传统文化”。投票结果的实质是:科学技术比传统文化更伟大——不,更有用!对的,我们的思维至今都离不开那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核心问题:“有啥用?”要知道,在从古希腊时期直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时光里,西方人对自然科学的思考研究也是没啥用的。那时自然科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宗教。在理论上问“有啥用”是中国人的特点,但是在现实中回答“有啥用”,是古今中外谁都逃不脱的命运。你答不出来,社会就不容你。在中世纪,哲学存在的理由就是论证上帝,自然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给哲学作注脚。哲学和自然科学正是依傍着宗教,才回答清楚了自己有啥用。崇拜牛顿的朋友们总不能连《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没读过吧,以下摘抄其《总释》篇:……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如果恒星都是其他类似体系的中心,那么这些体系也必定完全从属于上帝的统治,因为这些体系的产生只可能出自于同一份睿智的设计;尤其是,由于恒星的光与太阳光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来自每个系统的光都可以照耀所有其他的系统:为避免各恒星的系统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碰撞,他便将这些系统分置在相互很远的距离上。
上帝不是作为宇宙之灵而是作为万物的主宰来支配一切的;他统领一切,因而人们
惯常称之为“我主上帝”(παγτοκρατωρ)或“宇宙的主宰”;须知(上帝)是一个相对词,与仆人相对应,而且(神性)也是指上帝对仆人的统治权,绝非有如那些认定上帝是宇宙之灵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指其自治权。至高无上的上帝作为一种存在物必定是永恒的、无限的、绝对完美的;但一种存在物,无论它多么完美,只要它不具有统治权,则不可称之以“我主上帝”……
这些我都读不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神学,什么三位一体,所以不知道牛顿在说个啥。但是光看他三句话不离上帝,也能理解为什么说科学、哲学在那时是依傍宗教的。王阳明一边看花一边领兵打仗的时候,西方的最聪明的人们都在激烈辩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种辩论有啥用嘛!
然而漫长的“无用”过后,科学突然赢得了超越一切的“有用”,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生产力”。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的科学技术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般,神秘莫测,堪比传说中的巫术,居然到了能定点投放只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的地步。相比之下,宗教,哲学,艺术,传统文化,统统倒被扫进了“无用”的垃圾堆。看人家吃了第七个面包饱了,却没看到人家之前已经吃了六个,连自己手上正在吃的馒头都要扔掉,跟人家学着吃面包。中国的好还是西方的好,传统的好还是现代的好,这问题讨论下去太麻烦。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其实是:对于人类社会,是科学技术更有用,还是文化更有用?问得更赤裸一点,科学技术有用我们都知道了,文化呢?文化到底有啥用?自然界的种种,对人类最有用的莫过于空气,明明是赖以生存的东西,却能让人完全忽略它的存在。只有到了空气质量差的时候,人们才确切地感受到有“空气”这种东西。文化的命运类似于空气,它无所不在,却只有在散发恶臭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及伴随而来的不留余地的批判。要讲清楚文化有什么用,我终于又能回到这篇文章的起点,接着谈吃野味的问题了。前面我把吃野味追溯到了《山海经》,追溯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仿佛吃野味是根植于中国人文化基因深处挥之不去的梦魇。但是现实中,吃野味的人真的不多啊,难道我们不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吗?显然,“吃野味”的原因不单单在此。
小时候看过一个外国的童话故事,说一个公主也喜欢吃野味,她的野味非同凡响,她只吃百灵鸟的舌头,一顿饭要杀掉上百只百灵鸟。那时实在不懂,舌头能有什么好吃的?就算再好吃,顿顿都吃一样的东西,又有什么滋味?长大了才渐渐明白,这道菜根本无关乎百灵鸟的舌头,她吃的是财富和权力。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而不能享受,是非常难受的。明明拥有一顿饭吃一百只百灵鸟的社会条件,可是落实到自己身上,一顿饭根本吃不下那么多。于是解决方案出来了:只吃百灵鸟的舌头,这样既不会撑死自己,又享受到了一百只百灵鸟的充实感。据说当年罗马贵族穷奢极欲,发明了催吐剂以便能享受更多的美食,也是同样的道理。百灵鸟权力和财富,用马克思主义的叫法,都是“社会关系”。常言道:“良田百亩,日食三餐;大厦千顷,夜眠七尺。”当一个人拥有了享用不尽的社会关系时,小小的身体如何再能支撑起大大的欲望?豪车豪宅已经体现不出更高的社会关系了,那就把豪车开进故宫。美酒佳肴已经满足不了更大的消费欲望了,那就去尝尝野生动物,最好是受法律保护的,才能真正体现出他们高人一等。
虎骨能不能强身健体,其实他们未必较真,关键是这玩意儿又贵又难得。象牙能不能延年益寿,他们也并不在乎,只知道动物保护法让象牙越来越稀缺了,物以稀为贵,要是从活象身上取下来的“血牙”那就更贵了。《山海经》里的神奇动物我们找不到,于是就将现实中的濒危动物“食之”,“佩之”。人类社会永远有人站在财富和权力的顶端,他们纵情挥霍,任意生杀,说不清是人在操控着力量,还是力量在操控着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当然历史上早就有了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没别的,还是文化。公主顿顿都吃一百条百灵鸟的舌头,长此下去她自己也挺难受的,于是驯兽师告诉她:何不改成在吃饭时让一百只百灵鸟在旁边唱歌呢?这样既彰显了财富和权力,又不用傻折腾自己的胃口——于是文化就诞生了。文化把有限变成无限,把野蛮变成文明。正是文化,让金字塔拔地而起,让兵马俑结阵而来,让权力软化为礼法,让财富凝结成艺术。贵族们渐渐摆脱了被力量支配的傻折腾,开始参与到文明的自我展现中去。于是弱者对强者的害怕和顺从变成了尊敬,食利阶层的优越感也变得越来越合理。当年大汉初创,叔孙通为刘邦制定了朝堂礼仪,体验过后,刘邦感慨道:“才知道当皇帝原来这么爽啊!”文化有啥用?你问问刘邦去。话说回来,我们忘不了金字塔下流着奴隶的血汗,兵马俑里藏着生民的冤魂。文化有用,也要看给谁用。文化和其历史上的阶级属性之关系必须要掰扯清楚。有人把阶级仇恨转嫁到文化成果上,对本该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进行大肆破坏。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这里就不再加以批判了。有人把对文化的钦慕转化为对“贵族”的崇拜,这种思潮则会长久存在。不知从哪里传开一句话,说“中国有很多有钱人,却没有贵族了”,意在批判中国的暴发户没文化。可是,文化是文化,贵族是贵族。贵族的本质是什么?《诗经》里说得清清楚楚:“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贵族就是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世袭财富、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人。文化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它不限于贵族才能享受。在现代社会生为平民却呼唤“贵族”,我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还有一种人,把对“贵族”的崇拜,转化为了对权贵们的“傻折腾”和腐臭文化进行拙劣的模仿。恐怕当今吃野味的人中为数最多的就是这种。野味在今天虽然违法,却并不昂贵,恐怕也远远称不上美味。吃野味的人要么是为了在廉价的消费中感受到虚幻的特权,要么是真的信了特权的鬼话,以为稀奇古怪的东西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好处。这才是吃野味的直接原因。不同的文化决定了愚蠢的不同方式,但真正导致愚蠢行为的,还是愚蠢本身。食物就是权力,这一点在哪儿都一样。美国学者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分析了英国人嗜甜的饮食文化的来龙去脉,很有意思。早期全世界蔗糖产量很低,甜食是贵族的特权。女王拥有无穷无尽的糖,并且常常恩赐糖块给近臣,糖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奢侈品,你家的糖越多,就说明你离权力的中心越近。后来美洲种植园的大规模开发,使蔗糖变得廉价,人人都得以享用。而甜食代表尊贵的文化意义却保留了下来,于是各个阶层的人都怀着对权力和财富的崇拜,对甜食趋之若鹜。甜食成为文化习惯也没什么不好,且不说它真的可以做到十分美味,只要别太过量,吃甜食于人于己也都没什么害处。但野味成为文化习惯,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如病毒的肆虐不能归罪于武汉人,畸形愚昧的思想也不能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在一线医务人员的英勇奋战和举国劳动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消灭野味肺炎只在旬月之间。至于消灭野味文化,则需要有识之士打一场持久战了。(图片均来自网络)作者
李四维编辑
凌篁
长安诗社
changanshishe
打·造·传·统·文·化·旗·舰
读者
投稿:changanshis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