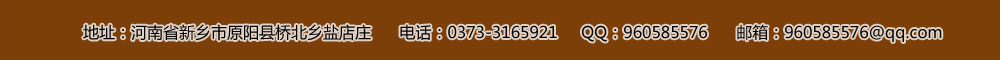中原王朝对于台湾地区的管辖
关于中原王朝与台湾地区的交流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有关于台湾的较早记载见于《三国志》,根据《三国志吴书》所载: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黄龙二年(公元年)正月,孙权派遣将军卫温与诸葛直率领士兵乘船探求夷洲和亶洲。由于亶洲路途遥远,最终没有能够到达,只俘获了夷洲数千人。这里的夷洲就是指台湾岛。
在同时代的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夷洲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好以为饰也。从此文中亦可看出,夷洲当为台湾岛,并且也可以看出此时岛上的原住民仍然处于原始社会。以上两段史料是大陆地区同台湾地区交流之始,此后中原王朝同台湾的交流日益频繁起来。
在隋代时,虎贲将陈棱曾经率领军队到达过澎湖列岛,见于魏源的《圣武记》:
台湾亘闽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距澎湖约二百里、厦门约五百里。隋开皇中,虎贲将陈棱一至澎湖,东向望洋而返。此时台湾岛称为“流求”,《隋书列传卷四十六东夷传》记载: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硃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郤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从《隋书》的记载可见,在隋大业年间,隋炀帝三次派遣军队前往征讨流求,而这三次并没有征服流求,只是俘虏岛上数千人便返回大陆。不过对于陈棱所到达的流求是否是如今的台湾岛在不同的史籍上有所争议,根据《澎湖厅志卷二》记载:
澎湖在福建布政司东南大海中,东距台南府水程四更,计一百七十里。西北距会城港口约十更;西距厦门七更,约三百三十余里;古荒服地。隋大业中,遣虎贲陈棱略地至澎湖。在《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流求传》中也有对于流求的记录,并且在其中还记载有:
其境在漳、泉、福、兴界,与彭湖诸岛相对,西、南、北岸皆水,水至澎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镖,瓦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风漂流落潦,回者百一,故其地小而最险。从该文中可推断,流求与澎湖列岛相对,流求当属台湾岛无疑。
并且《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流求传》中又有:
流求......历唐、五代,皆与中国绝。从该记载可看出,隋之后,宋之前,台湾岛同大陆之间的往来中断了,并且此时中原王朝并没有能够在台湾地区建立统治与管辖机构,真正最早在台湾地区行使管辖权的中原王朝是南宋。
唐宋时期,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多及航海技术的发展,在福建等地的大批汉人向台湾地区的澎湖列岛进行移民活动。随着在澎湖列岛汉民的不断增多,为了保护澎湖岛上的人口不受侵犯,南宋政府开始对澎湖列岛进行管辖,在那里修建房屋,驻扎军队。在南宋周必大的《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大猷神道碑》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有毗舍耶蛮,扬帆奄至,肌体漆黑,语言不通,种植皆为所获,调兵逐捕,则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为乡导,劫掠近城赤屿洲。于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劳费不赀。公即其地造屋二百区,留屯水军,蛮不复来。这里的平湖即为澎湖列岛,汪大猷时任泉州知州,从该文中可见,此时澎湖列岛上已有南宋军队驻扎,并且澎湖列岛此时属泉州府管辖。
在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一书中记载:
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这些记载都毫无争议地说明了澎湖列岛归南宋所统治。
虽然澎湖列岛已归属中原王朝管辖,但是对于此时的台湾岛而言,南宋政府并未实际控制及治理。在宋代,台湾岛有多种说法,一说流求国,一说毗舍邪国(一说毗舍邪国指菲律宾)。据《宋史列传卷二百五十》所载:
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国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植棘为藩,以刀槊弓矢剑铍为兵器,视月盈亏以纪时。无他奇货,商贾不通,厥土沃壤,无赋敛,有事则均税。旁有毗舍邪国,语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类。从该记载所看,流球国与澎湖列岛相对,当为台湾岛,毗舍邪国照此记载推断也应在台湾岛上。,由此观之,流求国与毗舍邪国当同属台湾岛之一部。另外,在不同的书中关于台湾岛的称呼也并不统一,《台湾小志》所记:
《宋史》载:彭湖东有毗舍那国,即台湾岛也。从《台湾小志》一文中指出《宋史》中的毗舍那国即台湾岛。《诸蕃志》一书中记载:
毗舍耶,语言不通,商贩不及,袒裸盱睢,殆畜类也。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时至寇掠。其来不测,多罹生啖之害,居民苦之。从这里可以看出,毗舍耶与澎湖列岛相对,并且距离很近,当为台湾岛无疑,并且也可以看出此时在台湾岛上的原住民也曾与大陆地区有过冲突摩擦。例如在《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流求传》中就有记载:
宋淳熙间,琉求巨豪率数百人猝至泉州水澳围头等村杀掠,人闭户则免,刓其门圈以去。掷以匙箸,则纵拾之。见铁骑,争刓其甲。官军追袭之,泅水而遁。到了元代,由于元吞并了南宋,自然澎湖地区也归元政府所管辖,大元至元年间(据考证,此至元为元顺帝年号,而非元世祖忽必烈年号之至元),元政府在澎湖地区设置了澎湖巡检司,隶属于泉州晋江县管辖(一说隶属于泉州同安县)。关于元设置澎湖巡检司一事在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在元朝江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有:
至元间,立巡检司。在《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岛夷诸国》中记载:
海外岛夷之族,澎湖最近,分三十六岛,有七澳介其间。其地属泉州晋泉县。土人煮海为盐,酿林为酒,采鱼虾为食。至元初,设巡检司,东为琉求,与澎湖相对。在清代谢金銮的《续修台湾县志》中曾明确提到:
元之末,于彭湖设巡检司,以隶同安,中国之建置于是始。从这里可以看出,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是中原王朝在台湾地区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的开始,此时的澎湖巡检司行政级别很低,所谓的巡检司一职,始于五代后唐庄宗时期,品级很低。在《新元史卷五十五志第二十九百官八》中详细记载了各个官职的品级:
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一员,正六品。尹一员,正六品。丞一员,正八品。簿一员,正九品。尉一员,从九品。典史一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下县,秩从七品。置官如中县,民少事简之地则以薄兼尉。后又别置尉,主捕盗之事,别有印。典史一员。巡检司,秩正九品。巡检一员。从《新元史》的这段记载中可见,巡检司是品级最低的。
在《文献通考卷五十九职官考十三》中记载有巡检的职能:
宋朝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又巡马递铺、巡河、巡捉私茶盐等,各视其名分,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机察之事。中兴後,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皆以才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本寨事并用取州县指挥。若海南琼管及归、峡、荆门等处跨连数郡,控制溪峒,又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以增重之。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巡检司是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因此澎湖巡检司的功能主要是训练士兵,缉捕盗贼,维持澎湖地区的秩序与日常治安,并且对于澎湖地区的诸岛屿进行日常巡逻。另外,澎湖巡检司兼具收税的职能,见于《岛夷志略》一书:
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那么此时元政府对于台湾岛有无管辖权呢?元朝对台湾岛曾有过两次军事行动,据《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流求传》所载: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船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则受之,不听命则伐之。朝迁从其请,命祥为都元帅,将兵抵其国。有书生吴志斗者,上言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若欲收附琉求,且就澎湖发船前往,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乃命祥充宜抚使,志斗假礼部员外郎,捧诏以行。诏曰:“朕收抚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诸番罔不臣属,惟琉求密迩闽境,未曾归附,议者请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国先遣使招降,来则安堵如故,否则必致征讨。今命使宣谕尔国,果能慕义来朝,存尔国祀,保尔黎民。若不效顺,自恃险阻,舟师奄及,恐胎后悔。尔其慎择之。”明年三月,自汀州尾澳东行,至海洋中,远望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言是琉求,独乘小舟至山下,见其部众。令军官刘间等二百馀人,以小舟,偕三屿人陈辉登岸。众不解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还至澎湖,觅志斗弗能得。初,志斗尝斥言祥生事邀功,言诞妄难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顾称志斗惧诛逃去,志斗妻子诉于官,敕发福建行省置对。后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元贞三年,福建行省平章高兴言琉求可图状。遣省都镇抚张浩、新军万户张进赴其国,擒生口百三十人而返。自是,终元之世,史不再见也。从上述记载来看,元时期对于台湾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收获不大,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这里说直到元灭亡也不再有关于台湾岛的记载,但是实际上在《元史本纪第十九成宗二》中仍然可以见到相关记载:
大德元年......二月甲午朔......平章政事高兴言泉州与琉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福建行省遣人觇琉求国,俘其傍近百人以归。二年春正月壬辰......遣所俘琉求人归谕其国,使之效顺。从《元史》和《新元史》上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元政府并没有建立对台湾岛的统治。正如《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一百五十流求传》所写的那样:
史臣曰:琉求今之台湾。今之琉求,至明始与中国通。或乃妄合为一,误莫甚矣。很明显,这张图错误地将台湾岛划入元朝版图
不过虽然元朝政府并未实际控制台湾岛,但是台湾岛同大陆居民的往来贸易已相当成熟,见于《岛夷志略》:
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黄、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这是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元至元十七年地图,未将台湾岛纳入版图
到了明代,明大体沿袭元制,继续在澎湖列岛上设置澎湖巡检司加以管理。不过在之后,澎湖巡检司被废除,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
明初洪武五年,汤信国经略海上,以岛民叛服难信,议徙之于近郭。二十年,尽徙屿民,废巡司而墟其地。继而不逞者潜聚其中,倭奴往来停泊取水,亦必经此。从上述记载可见,由于澎湖地区的民众经常叛乱,为了加强管理,开始商定废除澎湖巡检司,直到洪武二十年(《澎湖厅志卷二》记载为洪武二十一年,从成书年代来推断,《澎湖厅志》的记载当为谬误),终于将其废除,澎湖地区成了荒地。但是此时处于无人状态的澎湖列岛便成为了罪犯理想的藏身之处,并且也成了当时倭寇的中转站。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东海沿海一带的倭寇和海盗日益猖獗,为了打击其中的林道乾一部,嘉靖四十二年,明朝抗倭将领俞大猷(与同时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在澎湖地区驻扎军队进行驻防,但这一举措是临时性的,随着林道乾的逃遁,驻扎在澎湖地区的军队也随之撤离。见于《台湾旧志》:
嘉靖四十二年,林道乾寇乱边海,都督俞大猷逐道乾入台。侦知港道纡回,法不轻进,留偏师驻澎;时哨鹿耳门外。道乾既遁,澎之驻师亦罢。虽然军队撤离,但是明政府在澎湖地区重新设置澎湖巡检司以加强该地区的管理,由于澎湖列岛远离大陆,交通不便,澎湖巡检司再次被废,见于《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道乾既遁,澎之驻师亦罢,因设巡检守之,既以海天遥阻,裁弃。万历二十五年七月,福建巡按向万历皇帝上奏折,陈述由于澎湖地区距离泉州很近,如果不对澎湖加以管理的话,恐怕会成为倭寇的巢穴与根据地,所以建议朝廷在澎湖地区设置军队加强防御,该提议得到批准,不过此时只是在汛期到来的时候才驻军,汛期一过,即撤军。见于《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二》:
乙已,福建巡按金学曾条上防海四事。一、守要害;谓:倭自浙犯闽,必自陈钱,南麂分口。台、孀二山乃门户重地,已令北路参将统舟师守之。惟彭湖去泉州程仅一日,绵亘延袤,恐为倭据;议以南路游击汛期往守。一、议节制;谓:福建总兵原驻镇东,但倭奴之来皆乘东北风,福宁、福州乃其先犯,镇东反居下游;欲将总兵于有警时移割定海,以便水陆堵截。一、设应援;造大小战船四十只、募兵三千名,遇急分投应援。一、明赏罚。部覆,允行。万历二十五年,明政府在澎湖列岛增设游兵,游兵是明代的一种基层的军事单位,不过此时的军队只是在春冬汛期时驻守。万历四十五年(一说万历三十五年,见于《漳州府志》),由于倭寇入侵龙门港,于是在澎湖地区的军队开始长期戍守,并且增设了冲锋游兵抵抗倭寇。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
二十五年,增设游兵,春冬汛守。四十五年,倭入犯龙门港,遂有长戍之令,兼增冲锋游兵,以厚其势。不过,由于之后随着明军军纪废弛,澎湖守军经常“开小差”,加之明政府对于澎湖守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这就使得澎湖列岛上的游兵名存实亡。见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九条议海防事宜疏》:
一重要防以杜窥伺,闽海中绝岛以数十计,而彭湖最大。设防诸岛以十余计,而彭湖最险远。其地内直漳泉,外邻东番。环山而列者三十六岛,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据之可以制倭倭据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谓必争之地也。......当事者始建议戍之,镇以二游,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余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偏师,穷荒远戍,居常则内外辽绝,声息不得相通,遇敌则众寡莫支,应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视之,后汛而往,先汛而归,至有以风潮不顺为辞,而偷泊别澚者,则有守之名,无守之实矣。明朝中后期,由于荷兰殖民活动的扩张,势力已达到台湾地区。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荷兰人韦麻郎率领两艘船到达澎湖,之后在和明军将领沈有容的谈判下撤出澎湖。万历三十七年,又有一艘荷兰船到达澎湖列岛,在澎湖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开。
到了天启二年六月,荷兰人趁着澎湖列岛上防卫空虚,一举占领澎湖地区,在其地修建城堡,进行防守,之后在同当地守官谈判下又毁城撤出。从天启二年至天启四年,荷兰人反复袭扰澎湖地区,之后在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遣总兵俞咨皋(根据《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四十七》(梁本)记载,还有守备王梦熊,把总洪应斗等人)同荷军交战,重新收复澎湖,澎湖地区得以重归平静,见于《漳州府志》:
天启二年外寇据澎湖,四年巡抚南居益遣总兵俞咨皋擒其渠帅,献俘于朝。这场战役的意义,诚如《明清史料戊编卷一彭湖平夷功次残稿》所言:
是役也,曾无亡矢遗镞之费,血刃膏野之惨,而彭湖信地,仍归版图,海洋商渔,晏然复业。此固仰藉宗社之灵,乃本抚院正气参天,殊勖揭日,措全闽于泰山之安,结前抚两年拮据之局。并且为了使澎湖列岛不受荷兰人的再次侵犯,明军在该地修建城池炮台,驻扎军队,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
自万历三十七年,红夷(即荷兰人)一舟阑入彭湖,久之乃去。天启二年六月,有高文律者,乘戍兵单弱,以十余船突据彭岛,遂因山为城,环海为池,破浪长驱,肆毒于漳泉沿海一带,要求互市,欲如粤东香山澳夷例。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于北港,乃得复彭湖。议于稳澳山开筑城基,通用大石垒砌,高丈有七,厚丈有八。东西南共留三门,直北设铳台一座,内盖衙宇营房,凿井一口,戍守于此,以控制娘宫。对于这一时期在澎湖地区所驻军队具体情况也见于《明史兵志卷三》
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从上述史料可以得知,此时的澎湖守军重新得到了恢复,较之前只在岛上设置游兵的举措而言,这次对于澎湖的管辖更加完善,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明政府此时已较为重视澎湖地区了。
然而此时由于明朝已经到了快要灭亡的地步,东北边患日益严峻,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国库空虚,明政府对于东南地区已无力经营,也不能再维持澎湖地区的军事开支了。在天启之后,澎湖列岛终被荷兰人占据,直到明朝灭亡。该记载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
然议者谓彭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即彭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不特彭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天启以后,皆为红夷所据。这是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万历十年福建台湾地图,此时未将台湾岛纳入明版图,右下角为明郑时期的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说完了明时期的澎湖列岛管辖问题,对于与澎湖列岛相对的台湾岛属于明政府管辖吗?据《明史列传卷二百十一外国四》所记载,在明代建立之初,洪武五年甲子,朱元璋派遣杨载到达琉球群岛中的中山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在所带去的这篇诏书中将此地称为琉球。此可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束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自此,为了以示区分,将琉球群岛称为大琉球,台湾岛称为小琉球。见于日本人藤田丰八的《岛夷志略校注》:
明初中山王朝贡受封,自是冲绳列岛(即琉球群岛)称大琉球,台湾称小琉球。此时的台湾岛仍未得到明政府的重视,占领台湾岛对于统治者而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在洪武二十八年重新修订的《皇明祖训》中记载: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小琉球国(不通往来,不曾朝贡)......从该文知,此时的台湾岛对于朱元璋而言,仅仅是蛮夷之地,得不偿失,况且对明朝构不成威胁,所以列为不征之国,后世子孙也不必征伐,因为没什么价值嘛。因此在明代初年,台湾岛没有纳入明政府管辖之中。
到了永乐年间,郑和在朱棣的支持下,率领庞大的舰队南下炫耀明代国威,曾经到达过台湾。据《台湾小志》记载:
明成祖永乐末年,遣太监王三宝至西洋,遍历诸邦,采风问俗。宣德五年,三宝回行,近闽海为大风所吹,飘至台湾,是为华人入岛之始。越数旬,三宝取药草数种,扬帆返国,后无问津者。在《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中记载:
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即台湾岛)远避不至。和恶之,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富者至掇数枚,曰:“此祖宗所遗。”在《明史》中可见,郑和船队到达过台湾,并且还用铃铛羞辱当地人。郑和到达过台湾这一说法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他们考证郑和并未到达过台湾岛,不过台湾至今仍流传着不少关于郑和的传说,孰真孰假,随着岁月的变迁已变得扑朔迷离。
到了明代中后期,此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种势力轮流登台,使得台湾地区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是倭寇大规模袭扰东南沿海地区,在明军的大力打击下,倭寇不得不撤退到了台湾岛。为了消灭倭寇,万历三十年,在明军将领沈有容的带领下,明军乘船渡海,前往台湾岛。见于《平东番记》:
顷倭奴来据其要害,四出剽掠,饱所欲则还归巢穴......时语屿偏将军沈君有容,受中丞国士知。其人慷慨义侠,有古烈士风......适朱公有密札与君,令剿东番倭......从彭湖又行一日夜,纔抵东番,则倭奴已望见我军,出舟迎敌。将军率诸将士殊死战,无不一当百;贼大败,尽出辎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而姑少缓师。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战益力,斩诚火攻,须臾而尽。东番夷酋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咸以手加额,德我军之扫荡安辑之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明军在台湾岛同倭寇激战,大败倭寇。并且在击败倭寇之后,台湾当地的部落人民纷纷犒劳明军将士,随军的陈第将台湾岛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东番记》,这是记录台湾岛上原住民生活的珍贵历史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题东番记后》中写道:
假令不有沈将军今日之巨功,吾泉人犹未知有所谓东番也......国家承平二百余年矣,东番之入纪载也,方自今始,不可谓不奇。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明朝东南沿海居民来说,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有台湾岛的存在,不过这里与其它史料的记载有出入。根据《平东番记》所写:
东番者,彭湖外洋海岛中夷也。横亘千里,种类甚繁;仰食渔猎,所需鹿靡,亦颇嗜击鲜。惟性畏航海,故不与诸夷来往,自雄岛中。华人商渔者,时往与之贸易。可见,渔民商人同东番地区的部落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东番的存在了。
在《东番记》中有写:
万历壬寅冬,倭复据其岛,夷及商、渔交病。语屿沈将军往剿,余适有观海之兴,与俱。倭破,收泊大员,夷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献鹿馈酒,喜为除害也。予亲睹其人与事,妇语温陵陈志斋先生,谓不可无记,故掇其大略。大员即明代的大员港,位于台湾岛西南部的嘉南平原,也即北港,可见此次明军是在台湾岛西南地区登陆,从《题东番记后》中可看出,这也应当是明军登陆台湾岛的最早记录。但是对于明军而言,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打击倭寇,并没有在台湾岛驻军管辖,纳入明朝版图的想法。
虽然明代官方对台湾岛并未进行过多干预,但是有明一代,民间与台湾岛之间的交流却一直存在着,并且在很早的时候便开始开发台湾岛了。在《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所载:
台湾在澎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程…...初,贫民时至其处,不过规鱼猎之利已耳,后见内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并且大约在明万历、天启年间,就有不少的福建沿海居民向台湾岛进行移民,这些移民甚至已经和当地的原住民进行通婚。
这些开发台湾岛的移民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颜思齐。颜思齐是福建海澄人,后来前往日本,被任命为甲螺(头目),后来由于密谋推翻日本幕府统治,计划泄露,不得不逃离日本。据《台湾通史史卷二十九》所载:
思齐既谋起事,事洩,幕吏将捕之,各驾船逃。及出海,皇皇无所之。衷纪进曰:“吾闻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馀之业可成也。"从之。航行八日夜,至台湾。入北港,筑寨以居,镇抚土番,分汛所部耕猎。......芝龙昆仲多入台,漳泉无业之民亦先后至,凡三千馀人。颜思齐率领部下在台湾岛的北港登陆,在这个地方修建城寨,对台湾岛实行统治,进行屯垦,并且福建沿海的无业民众也纷纷前来,形成了一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使得颜思齐被称为“开台王”。
在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接替颜思齐,成为台湾的统治者。之后在崇祯年间,郑芝龙接受明政府的招安,据《台湾通史史卷二十九》所载:
崇祯元年春正月......七月,泉州太守王猷遣人招抚,芝龙从之,率所部降于督师熊文灿,授海防游击。此时由于台湾在郑芝龙的统治下,而郑芝龙为明政府的下属的海防游击,从名义上可以说这个时候明政府具有了对台湾岛的管辖权。
这个时候的台湾的诸多港口得到了开发,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一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鸡笼、淡水、北港。
在之前已经讲过,台湾岛在元代时便已经同大陆、澎湖地区进行着贸易往来,而到了明代,这一贸易变得更加频繁。在琉球国同明朝确定朝贡关系后,位于中琉之间的鸡笼、淡水成为了两国交流的枢纽。此时在各种史料典籍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鸡笼的记录,说明此时的鸡笼、淡水成为来往两地的重要中转站和地标。不过这一时期鸡笼、淡水的贸易并不太发达,应该是由于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导致的。
到了明朝中叶,此时海禁政策开始有所松动,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年间海禁政策的解除,这使得东南沿海一带的贸易变得异常活跃起来。《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记载:
鸡笼山(即鸡笼)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迩......嘉靖末,倭寇扰闽,大将戚继光败之。倭遁居于此,其党林道乾从之......而鸡笼遭倭焚掠,国遂残破。初悉居海滨,既遭倭难,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国渔舟从魍港飘至,遂往来通贩,以为常。在倭寇摧毁鸡笼之后,汉人重建鸡笼港,在隆庆万历年间,鸡笼又成为了贸易港口。另外,在鸡笼附近的淡水港也得到了开发。《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记载:
水道,顺风,自鸡笼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达。可见,鸡笼、淡水在明代已成为了来往大陆与台湾的一个港口。另外,在这一时期,日本人也来此地进行贸易交流。随着鸡笼、淡水两港的贸易日趋发达,明政府向前往鸡笼、淡水两港贸易的人颁发船引,归入政府管辖之中。而所谓的船引就是在开放海禁之后,为了向商船征收税额,明政府所颁发的出海经商证明。见于《敬和堂集》记载:
同安、海澄、龙溪。漳浦、诏安等处奸徒,每年于肆伍月间告给文引,驾使鸟船,称往福宁卸载、北港捕鱼,及贩鸡笼、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潜去倭国,徂秋及冬,或来春方回。从该文也可知,此时来往中日之间的贸易及走私也十分猖獗。
之后,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扩张,他们把眼光聚集到了鸡笼、淡水。在天启六年,西班牙人陆续占领鸡笼、淡水作为它的殖民地,并在其地修建圣萨尔瓦多城和圣多明哥城要塞。不过西班牙人在鸡笼、淡水两港的经营不善,崇祯十五年,荷兰人攻占圣萨尔瓦多城,西班牙队台湾岛北部十六年的殖民历史宣告结束。
在鸡笼、淡水两港得到开发的同时,台湾南部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港。北港位于今天的台湾台南市,北港的开发源于其丰富的渔业资源,来自福建、广东一带的渔民是北港最早的开发者。姚旅的《露书卷十》有云:
鹿筋,乌鱼子,鳗鱼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来自北港番……又乌鱼,带鱼之类,皆咬尾逐队,千百为群。取者必徐举,听其去半后取,不然则绝网断绳而去。从这段描述中可知北港渔业资源之丰富。从上文中的沈有容抗击台湾岛上倭寇的记载中,也有北港的记录可推断,至少在万历年间,北港就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笔者推断应当在隆庆开关之后北港才逐渐发展起来。
另外,北港也有众多的鹿,据《东番记》所载:
冬,鹿群出,则约百十人即之,穷追既及,合围衷之,镖发命中,获若丘陵,社社无不饱鹿者。......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当地生活的原始部落经常捕获野鹿,并且闽粤地区的汉民经常同他们交换鹿皮、鹿角、鹿肉等资源。而这些鹿资源恰好是十分值钱的商品,这也就导致了大量的商人涌入北港,进行贸易,此时的北港开始由渔港向贸易港转变。
随着北港鹿皮贸易的不断发展,东南沿海的商人们开辟了一条从北港到日本的贸易通道,中日之间的鹿皮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这给商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商人们不满足于只进行鹿皮买卖,于是将市场逐渐扩大,各种货物纷纷涌进北港,成为一个中国同外国进行贸易的中转站,这进一步造就了北港的繁荣。
在上文提到的天启四年,荷兰同大明在澎湖之战后,荷兰战败,退出澎湖,转而去往台湾岛。在北港地区修建热兰遮城,之后又修建赤嵌城,开始在台湾岛的殖民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天启四年的澎湖之战与现有的明代史料显示有所不同。
据《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载,整场战役最终是以双方和谈达成协议,荷兰从澎湖撤离而告终。主要的协议内容为荷兰人撤离澎湖,建议荷兰去台湾,明政府同意与荷兰人通商。而这些内容在笔者所查阅的明代史籍档案中并没有记载,笔者推测可能是明人故意将这段谈判史实刻意隐瞒所导致的,和谈对于明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不过即使是这样,在一些历史记载中仍可见到一些蛛丝马迹,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福建五》所记载:
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于北港,乃得复彭湖。从这段语焉不详的记录中也可以印证《巴达维亚城日记》的记载。那么由此,在天启四年,荷兰人实际上先于明政府在台湾岛建立起了正式的政府组织。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明政府对于台湾岛并不重视,对于澎湖列岛反而却十分上心,不惜与荷兰殖民者开战。天启四年是荷兰人殖民台湾之始。
不管是西班牙还是荷兰的殖民者,此时他们在台湾只是拥有几个据点而已,台湾岛开发的地区仍然主要处于郑芝龙的统治之下。彼时的郑芝龙控制着东南沿海地区,来往的商船都需要出钱购买郑芝龙的旗帜,否则便会遭到抢劫。见于《台湾通史史卷二十九》:
芝龙幼习海,群盗多故盟,或在门下。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舳舻直通卧内。所部兵自给饷,不取于官。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以故郑氏威权振于七闽。郑芝龙的势力之大,连荷兰殖民者都无法匹敌,在崇祯六年的料罗湾海战中,荷兰人惨败,郑芝龙所部大胜,进一步确立了郑芝龙在东南沿海,在台湾地区的霸主地位。不过在南明隆武二年,随着郑芝龙降清,他在台湾岛上的势力顿时陷入混乱状态,此时荷兰人趁机占领了这些地区,由此,台湾处于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之下了。
直到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领军队进入台湾,进攻热兰遮城,经过一番激战之后,荷兰殖民者最终投降,之后郑成功的军队北上进攻鸡笼、淡水,将台湾北部的荷兰殖民者也赶出了台湾。自此,盘踞台湾岛三十八年的荷兰殖民者被彻底赶出去了。由此台湾地区进入明郑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郑芝龙,荷兰殖民者还是郑成功,他们所控制的只是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地区的平原地带,对于广大的台湾岛中部和东部地区,并没有实际控制,仍然处于原住民的控制中。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领军队渡海进攻台湾,在拿下澎湖列岛之后,明郑迫于清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最终投降,明郑灭亡,清军占领台湾地区。此时,清廷内部就要不要在台湾地区设立机构控制台湾进行了一番争论。《清史稿施琅传》所载: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上命允行。有人认为台湾岛孤悬海外,对于清朝而言价值不大,建议把岛上居民迁徙至内地,弃岛。而施琅据理力争,上疏台湾岛不可弃,最终康熙采纳了施琅的建议。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布政使司,从此台湾地区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直到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将台湾地区割让给日本为止。
这是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清嘉庆二十五年福建台湾地图
台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这个自古的含义,我想引用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续编》中的一段话来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处理台湾问题就难了。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臣,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说一定要与中原正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行吗?不行。台湾当然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就是颜恩齐、郑芝龙一伙人。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但是,我们知道,郑成功于年收复台湾,那时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而郑成功则奉明朝正朔,用永历年号,清朝还管不到台湾。一直到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所以一定要说某一地区同中原正朝属于同一政权,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国的话,那末,台湾就只能从年算起,年前不算中国,这行吗?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高山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台湾自古以来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宾的地方,更不是美国的地方、苏联的地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方。但不是属于中原王朝,是属于高山族的,到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象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今天也正值谭其骧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谨以此文向谭先生致敬!
左家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