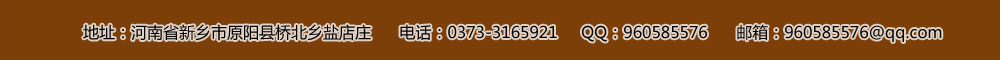对广州的偏见飞走了
落地广州,辗转到宾馆已经快夜里11点了,居然正撞上一帮朋友合计着出去宵夜。问我想吃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只要不吃福建人就行。”在场的有广东人很纳闷儿地问为什么要吃福建人。我就更纳闷了,难道广东人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对外形象吗?
第二天一早儿好奇地打开电视看粤语台,正好在播新闻,虽然听不懂,但是画面下面配着字幕。
第一条新闻是:
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在高速路上侧翻起火,消防官兵赶到时已经“烧得只剩铁架”。然后镜头一转,路面上成堆的螃蟹已经烤熟,这时主播的台词儿是:“想吃难吃,心痛至极!”可惜我不会粤语,特别是后四个字用粤语说出来铿锵有力。
第二条新闻是:
日前在广州某地突然经常有野生动物出现(从画面上看像是鹿),然后有人竟然架起电网,将路过的野生动物电毙,开膛破肚,架起炭火,正准备烤来吃,经举报后警方赶来,人赃并获。
看来广东人在“无所不吃”方面绝非浪得虚名。从而可以顺着“吃果子狸-吃福建人-吃外星人-没文化-荒蛮“的逻辑,顺理成章地形成鄙视链。因此,当华工的朋友说要带我去看一个南宋古镇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面无表情地问:
是说发现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吗?或者是客家村落?
不,是两千多年前(B.C.)为躲避秦军追杀而逃难至此的韩国贵族的后裔初创于南宋并兴旺绵延至今的沙湾何氏!
驱车临近古镇时看到路边”象贤中学“的牌子,敬意便随着好奇心腾起:能有如此气象万千的名字,必非等贤之地。
何氏大宗祠初建于元末,两度重建于明、清,里面供奉的沙湾何氏先祖,却可追溯至南宋徽宗年间的何棠、何栗和何榘三兄弟,人称“何氏三凤”。他们是公元前年逃至广东的韩国贵族的第五十代传人,而沙湾何氏则是大哥何棠的五代嫡系,即广东何氏的五十五代传人。
如此悠远而绵延不断的传承,足以打脸我的广东“没文化”的偏见。
补间五斗栱,一望便知是明清建筑无疑了。然而不设脊兽,以石柱为檐柱还是颇有南方古建之风,特别是改常见的一斗三升为一斗五升,更加增强了斗栱带的装饰性,虽说没了唐宋气象,在北方人看来却也十分稀罕。
木雕、灰雕、砖雕、石雕自是十分精美。除此之外,图案也有南方特色。下面是大门两侧户对基座的石雕图案。上图难道是”三羊开泰“?明明是三匹小马在玩耍;下图难道是鲤鱼跳龙门?
沙湾何氏人才辈出,在八百多年的传承中出了一大把举人、进士,论文化真真地甩晋商好几条大街。什么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跟何氏宗祠”留耕堂“相比,土得掉渣。
正堂迎门一匾”忠孝传家“为蒋中正所题,建国后被毁,后经研究复原;明间主匾上题”象贤堂“,象贤是沙湾何氏始居祖何明德的号,这个号起得我不得不服;明间前匾上题”大宗伯“,是指何明德长子何起龙(即沙湾何氏二代祖)官至南宋礼部尚书,正四品。
大宗祠门前广场上众多的旗杆夹,标榜着沙湾何氏在科举上的辉煌成绩。它们不是碑,而是成对设置,开有方孔,孔内插方木,可用来固定旗杆。
且慢,这是什么?
腊肉和咸鱼!干得漂亮!果然还是吃。
拎着垃圾桶穿行在小巷子里的老婆婆,让我想起出身江南的外婆。与北方的”大妈“或者”大娘“相比,在我看来,她们几乎是另一个人种。
如果只有冠冕堂皇的大宗祠述说曾经的辉煌,这里的魅力怕是要大打折扣。八百年延绵不断的传承不仅仅铸成了几块牌匾,几位名人,而且已经渗入日常生活,凝结成哪怕是一点点的文化,活着的文化。
锅
耳
墙
官名”镬耳墙“,镬(huo4)就是炒锅,镬耳说白了就是锅把儿。其功能大抵与徽州建筑中的封火山墙类似,只是仍然没离开吃。
在古镇,装饰精美的锅耳墙随处可见。倒也没有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加建时甚至可以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连接在一起,虽然看着不伦不类,却是真正地融入了时代的变迁。
蚝
壳
墙
下图不是海滩、碮岸和一望无际的大海;
而是墙面、屋檐和一望无际的天空。
就地取材,将蚝壳以黄泥、红糖、熟糯米为黏结材料,堆砌成墙,据说具有防火、防虫、隔音的功效,并且以其特殊的表面几何拓扑,便于墙面排水从而保持室内干燥。然而,还是没离开食物。
门
神
现存的留耕堂重建于清,以秦琼和尉迟恭作门神实属正常。二人皆为唐初名将,所以年代至早不会早于唐代。
然而在古镇民间,看家护院却仰仗历史更为悠久的门神:左神荼,右郁垒。他俩厉害到不必以形象驱邪,只用名字就够了。当地的一种说法是他俩虽然心底善良,但面目狰狞,实在太丑了,经常会吓哭小孩子,所以索性就只把名字贴在门上。这反而让我很想知道他俩到底长啥样儿。可惜我找遍了《山海经图纪》或者日本的《妖怪大全》也没找到他们的踪影。真可惜。
当然也有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家。比如这家,虽然已经褪色斑驳,仍能看出是左金童,右玉女。想必是求子心切吧。
财
神
古镇过年除了贴春联福字儿之外,还有贴财神的习俗。据说类似西方万圣节的TratorTrick,小孩子拿着写有“财神”二字的红纸条走街窜巷,贴到谁家门上,主人就要开门发红包。我去的时候正值公历元旦之前,许多家门上仍然残留着去年农历新年时贴上的财神纸条。
除了贴财神之外,对财神的尊重还体现在大门左下角对土地财神的供奉。下面这个视频只有十几秒,强烈建议点进去看一下,主要是听一下。
有没有看到在视频最后,随着镜头的转动,有一位老婆婆露了小半个脸?我在录这段小视频的时候完全没意识到屋里有人,估计这位老婆婆就那样坐在摇椅上静静地看着我认真地拍摄。当我摇起镜头看到她抻着脖子笑眯眯地望着我,竟然吓了一跳。
目测这位阿婆得有八十多岁了吧,然而她见我收起了手机,竟蹭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指着电视机跟我说了两句可能是粤语或是别的什么话,见我一脸懵逼,便招呼我进屋,蹬蹬蹬走到电视机前,从旁边的矮柜上拿起一个光盘盒给我看,上面写着《义释薄情郎》。原来她是想告诉我戏的名字。
即使不立牌位,在门口左侧焚一把香,也是对土地财神的尊敬。记起日本民间有在门口左侧放一小碟盐以辟邪的传统,居然都是左侧。
吃
最后还是绕不开吃。
与全国各地被铁板鱿鱼、大鸡排、臭豆腐……所充斥的“旅游景点”相比,沙湾古镇的地方小吃确实非常地方。连店名都起得不落俗套,一扫小清新文艺范儿,直接上兵器。
初见只觉得“针姨”这个名字很酷,爷们儿。于是决定试试。可一转念却想起来了容嬷嬷,竟然有些忐忑。
硬着头皮进店落座。原来这里既没有针姨也没有容嬷嬷,招呼客人并且亲自下厨的是一位大叔。我们基本是按照旗幡上点的:鱼皮角,狗仔粥,酿鲮鱼,凉拌鱼皮,另外加了一份网油春卷。非常对我们的口味,全部光盘!
心满意足之后再去街对面喝一碗浓浓的姜埋奶,驱散冬日的寒意。
紫禁城是死了的皇宫,晋商大院是死了的民居,西塘是死了的水乡,土楼是死了的碉堡,沙湾却是活着的古镇,它是靠什么活着呢?
做过很久的事情才能养成一点点习惯,
保持很久的习惯才能形成一点点传统,
积淀很久的传统才能凝成一点点文化。
陪我来玩儿的朋友说自己已经是第五次来这里了,并且还想再来!这次来去匆匆,只能走马观花。下次有机会我也还要再来。
这座小小的古镇,彻底改变了我对广州的偏见。
曲哲慢慢走,欣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