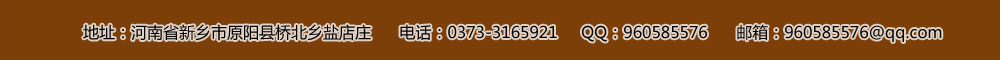新刊封底报道打工者的村庄
铁制的拱形门洞上挂着两个锈红色大字——“皮村”。因为早晨的一场雨,皮村主街的地面都是积水坑和泡软的泥,水坑里是泛着紫红色的水,泥地上则印着各种车辙的花纹。
街道只容得两辆三轮车交汇,两边是餐饮店和超市。正逢端午节,街上都是歇工放假的外来务工者。只有盖房的工人们没有停工,沿路不少房屋都被拆去,正进行原地重建。
一
“以前站在大街上瞅,三小时都不一定过来一人,”面馆老板王新近说,“过去一个还是老太太,从这头颠到那头,再从那头颠回来。”
王新近现年28岁,山西人。他18岁出来打工,到过河北河南,年来到北京。他熟悉餐饮行业,一开始在餐馆打零工,后来开始做厨师、掌厨。餐馆包吃住,但每月的花销总得超过两千。
不少餐馆都在年关张了,“以前干完一个月会发工资,后来老板经常压你,一压一个月。”后来,王新近所在的川湘菜馆也关门了。“我哥们干的店更次,最后他们把店里东西都卖了都没够他们工资。”
他感觉给别人打工不好干,便想自己开家饭馆。年冬天,他来到皮村,在主街租下一间店面开了家山西面馆,成了“王老板”。在那之后,又把在北京小厂里打工的父母叫来帮忙。
王新近在年冬天来到皮村,那时村里店面的租金还很低。摄
胡静漪
当时村里的本地人还想不到租房这项生意,“给多少钱算多少钱,不像现在房租一直往上涨。”王新近说。两年过去了,村口店面的租金如今已经翻倍,有些甚至涨了三倍。
现在,两万多人的皮村里只有10%的北京本地人,除了打工者,近年也有白领、大学生住进皮村。
皮村不少出租房都由二房东打理,他们出资让原房东重修房子,以抬高租金。四月份,王新近的面馆被原房东拆除,他只好另找店面房。新店面的装修花了一个多月,这次的店面不在主街,生意差一些。“我已经玩了一个月了。”他边打着手机游戏边说。
面馆不远处的房屋也正在原地重建。中午,面馆的来客都是工人们。王新近的母亲充当服务员,一笔一划地记录着每个吃客叫的面。她写字很吃力,总是记错对象和碗数,反复确认了四遍。
皮村离首都机场只有19.7公里,每十分钟,头顶都会有一架飞机轰鸣着经过,飞机飞得很低,用肉眼就能看到机身上的结构。正因皮村处于首都机场的飞机航线内,所以楼层有限制,无法盖高楼,因此皮村的租金涨得并不算快。
“三年内不会拆,楼盖不高,开发商不挣钱就不会干。”王新近说。
二
年,一个外地来的建筑工人到店里吃面,吃完就问“工友之家”在哪儿。这是王新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构。尽管就在同个村子,但他从没有去过“工友之家”,“就是外地农民工聚集地,我觉得也就是聊聊天,说说风土人情吧。”王新近说道。在他眼中,“工友之家”和皮村本地人无非是各说各话,相互间没什么来往。
从面馆往北米,穿过两条巷子,就能看到“工友之家”的院子。门口张贴着五六张手抄画报,最新的一张是端午晚会的宣传报。